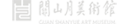- 关山月梅花辩
-
李伟铭
-
关山月什么时候开始画梅花?不清楚。
关山月开始引人注目的画梅作品,应该是1963年所画的《报春图》。在有些图录中,《报春图》也题为《写毛主席〈咏梅〉词意》。也许,当年老少能诵的毛泽东诗词,现在不少读者已经非常陌生了,现将其与本文有关的《卜算子——咏梅》引录如下: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词写于1961年12月,它还有一个小序:“读陆游词,反其意而用之。”为了突出与陆游完全不同的襟怀抱负,毛泽东在大作发表的时候,还将同题陆游词缀录其后:
驿外断桥边,
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
更着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
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辗作尘,
只有香如故。
不言而喻,梅花还是梅花;但因时代不同,身世、心境和所处社会地位有别,从梅花中看到的诗意和获得的认同感迥然有别,并不奇怪。毛泽东,开国元勋之尊,耸峙万仞,在傲雪欺霜的梅花那里,他看到的是一个革命的胜利者的形象;陆游,落魄文人,踯躅于穷途末路,除了孤芳自赏,普天之下还有谁能够理解他那份穷愁怨绪呢?所以,自叹自惜化为“咏梅”主题,也在情理之中。
自从梅花名列“四君子”榜首以来,多愁善感一族,从梅花单薄的花瓣中,多半嗅到的也就是陆游词提示的那么一种苦涩的芬芳。有趣的是,苏东坡赏梅,不忘怜香惜玉:“殷勤小梅花,仿佛吴姬面;暗香随我去,回首惊千片。”(苏轼)传诵千古的林和靖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写景,何尝不是写人——以一种怯生生甚至不无羞涩的心态,蹑手蹑脚接近高不可攀的梅花倩影。
于是,象临风飘举的白鹤,瘦峭、轻清,幽独,高洁,也就成了长期以来涉指“梅花”的专利语境:“昨夜尖风几阵寒,心知清物久难留;枝疏似被金刀剪,片细疑经玉杵残。”(刘克庄)“罗浮梦断杳无踪,冰雪仙姿两相逢。缟袂怯单寒后袭,粉妆嫌薄晓来浓。”(吴澄)……——诗人笔下的梅花,宛若呵气即化的轻雾或一梦已逝的情人——在吴澄那里甚至被赋予了那么一些“鬼气”。如老杜的“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这样的浊重、苍老,已是异数!
就一种大体的情形而言,在毛泽东以前的中国文化谱系中,“梅花”扮演的角色,不是洁身自好、高蹈远引的君子;便是冰清玉洁、可爱不可亵的女子。“画梅”,当然不能独立于这种经典的文化品味之外。文献中记载的李正臣继崔白之后,“不作桃李浮艳,一意写梅,深得水边林下之致”(《芥子园画谱——画梅浅说》),也是这种经典的品味的注脚。当然,岁月邅递,品味不能没有丝毫的变化。觉得“梅花愈老愈精神”的金冬心,画梅一若哑黯入定的老衲;近世名家吴昌硕、齐白石,笔下的梅花,直是老笔纷披之古籀或直截了当之篆刻。以画论画,后者距离古道,明显越来越远了。
“经典”是人创造的,何况毛泽东不是一般的人而是“神”。他笔下的梅花,既是自然时序更替的亲历者,也是波诡云谲的世界政治风云的见证人。关山月《报春图》所要参赞的,正是毛泽东那种富于挑战性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在“文革”中为他带来厄运的这件作品中,据实而言,“梅花”仅仅是点题之笔,真正富于说服力的是背景的铺垫:奇峭险绝的百丈悬崖冰雪,才是梅花之所以为“俏”和“俏”得令人惊心动魄的理由之所在。作为读者,与其说我们是在“赏梅”,倒不如说,我们正在“瞻仰”一个现代革命英雄主义者的精神归宿。而从学理上来说,源自关氏山水画风格的构图及其霸悍不可一世的用笔力度,则是直接构成“关梅”趋近于“毛梅”的推动力。关氏一反古人画梅遗意,其智慧的源泉不仅来自毛泽东的革命哲学的启发,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山水画家,他充分地发挥了善于营造整体氛围的艺术语言技巧。如《报春图》所示,由于突出了冰封雪冻、峰岳峥嵘的特殊环境,“梅花”作为一个现代革命英雄的品格与风度,才获得了卓有成效的强调。
奇险的构图,雄健的笔力,并且,所有这一切都倾向于在整体上追求咄咄逼人的气势和疾速运动的节奏,是关氏画梅的风格特征。陈子庄在《石壶画语录》中,曾对关氏画梅的美学价值提出质疑。其实,陈氏追求笔墨、意境的轻清、冲淡,与关氏强调的刚健、霸悍,南辕北辙;后者所画,不入前者之眼,容易理解。不过,若以陈氏之规,度关氏之矩,则未免有失公道;反之亦然。在这里,笔者感兴趣的,仅仅是决定关氏选择的那些细节。如所周知,《报春图》所以在文革中受到激烈批判,并非缘乎关氏无可非议的革命动机,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现代文字狱的制造者看来,画中由上而下倒挂生长的梅花——即“倒梅”,使人联想到革命时代一个无法容忍的字眼——“倒霉”。而从构图上来看,强调倒挂的梅枝与拔地而起的冰峰雪岳逆向的力度冲突,正是关氏别出心裁的匠心所在,在他差不多同一时期完成的作品如《疾风知劲草》、《东风》中,也可以看到这种令人错愕的形式语言。然而,毕竟“倒霉”的教训太深刻了,七十年代初期,关氏复出画坛,所画梅花,一反旧态:花繁枝密,枝枝挺拔向上——赞美革命英雄主义情怀,扩大而为歌颂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个中意蕴,还有赵朴初词为证:
对飘风骤雪乱群山,
仰首看梅花。
叹峻空铁骨,
荡胸灵气,
眩目明霞。
任汝冰悬百丈,
一笑暖千家。
不尽春消息,
传向天涯!
且试登高临远,
望丛林烈焰,
大漠惊沙。
指看云破处,
残霸枉纷□。
春弥天红旗一色
听四方八面起欢哗。
愿长此,
乔松劲健,
新竹清嘉。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咏梅,调寄八声甘州,山月同志为作画,并属题,朴初。
“赵词”、“关画”表明,这种主题的转移,正是通过相应的形式的变化,得到两全其美的实现。关山月是人,不是“神”,他毕竟无法用自己的画笔,来改变他所处的时代被某种“革命的迷狂”推向极致的美学标准。
众所周知,在那个处于非常时态的“革命”时代,在中国花鸟画艺术的园地中,允许艺术家栽培和发挥想像力的物种,除了搏击长空的“苍鹰”、傲雪怒放的“红梅”和宛若革命圣火的杜鹃花——“映山红”,大概没有别的选择。与其说,关山月从一开始就热爱画梅,倒不如说,“梅花”选择了关山月。七十年代的关氏梅花,固然为作者赢得了家喻户晓的巨大声誉,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始不能看成一个善于审时度势的艺术家,在逆境中实现自我保护并由此而使自己的艺术生命得以延续的有效方式。易言之,最能够体现关氏画梅的创造性的作品并非完成于七十年代,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那种铺天盖地,繁密得无以复加的红花和枝枝挺拨向上的嫩条,束缚和掩盖了关氏奇崛峥嵘的个人气质。关氏画梅的创造性获得真正充分的释放,还是在八十年代开始以后,特别是在丁卯(1987)除夕在六尺旧纸上用乾隆古墨所画的那件题为《天香赞》的长卷中,关氏以迅雷奔骤的取势和狞厉恣肆的笔法,画出了一个饱经苍桑的中国艺术家胸中的郁勃之气。与七十年代的画梅比较,八十年代以后的作品花头减少了,挺拨的嫩条一变而为披鳞带甲的古干和奇崛刚健的老枝。关氏也尝试纯以朱砂写梅,但并不多作,相反,他更乐于选择墨梅。他显然不再拘于朱砂为花、焦墨作干那种在视觉上两极反差强烈的形式;强调用笔、用墨的力度和层次,使其画梅在视觉和节奏感上出现了更为丰富的变化。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关氏在《天香赞》题跋中写道:“画梅不怕倒霉灾,又遇龙年喜气来;意写龙梅腾老干,梅花莫问为谁开。”可以肯定,在关氏这里,“莫问为谁开”并非漫无目的的信手涂抹,在一些重大的历史变化时刻,仍然可以看到关氏以“画梅”这一形式来抒发他的内心情怀———如《香港回归梅报春》(1997);但也必须承认,那种历经劫火、劫后犹存的大自在心境,无疑是促成其放笔直取的内驱力。
显而易见,关氏画梅的美学风格,是其山水画艺术合乎逻辑的延伸。正像他特别擅于驾驭巨幅山水画创作一样,其最为引人注目的画梅之作经常是一些寻丈巨制。1987年画于羊城流花湖畔的《国香赞》,实际上也可以看成一件巨幅山水画。笔者当年曾有机会目睹这件作品完成的过程,发现他也像画山水一样信守“九朽一罢”的原则,先设计草图,反复推敲画面体势大要包括款题位置,再据草图用木炭在宣纸上确定画面构图,然后才大胆落墨。绘画过程中,又并非依样草图,而是根据笔墨走势随时作出适当的调整。《国香赞》,原定用墨线圈勾白梅,但画了一半,发现视觉效果并不理想,乃改用朱砂勾勒,这样就出现了同一株梅,混用墨、色勾花的结果。值得指出的是,关氏创作过程中动脑的时间往往多于动手的时间,他经常远距离观照画面,不断调换观照角度,有时也会征询周围的人的意见,认真思考,考虑成熟后才抓笔落墨。其选择绘画枝干的毛笔,看上去应是陈白沙喜用的“茅龙”;写巨干,笔锋常作侧卧拖曳,细枝则逆锋缓行,以臂运腕,似乎运用了全身的力量。
必须承认,关氏画梅是源远流长的中国画梅谱系中的“新品种”,传统梅花之作固然没有关氏这样的鸿篇巨制,关氏狞厉张扬充满扩张感的美学品格,也很难在一尚温柔含蓄的经典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徐青藤有云:“从来不写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不信试看千万树,东风吹着便成春。”这种任才使气的胸襟,也许能催生出不拘一格、旷绝千古的杰作,但在青藤传世的梅花中,毕竟无缘看到画如所言的剧迹。据说,传世青藤的设色梅花,仅得两件,广东省博物馆所藏的那一件,无非是栖身四尺三开条幅、聊可插瓶的折枝嫩条而已,远不能再现青藤天风吹海雨一样的怀抱。关山月呢?关于他的梅花,肯定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但我可以肯定,正像“革命”是一个被赋予现代意义的古老概念一样,关山月笔下的梅花“关梅”也是对传统画梅艺术的一种新的诠释,只要艺术史还没有全部丧失其实事求是的品格,关氏的梅花就应该占有令人无法漠视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