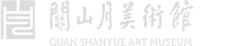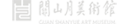- 名家点评
-
-
邵大箴(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丁观加善于处理空间,注重构图的角度和深度,在近景中加以穿插,表现深远的空间,不论是经营位置的变化均衡,还是线的方圆、粗细,墨的燥湿浓淡,色的明暗寒暖,在他的画面上,均紧紧服从于表现客观物象特有的美和表现自己的主观感情,服从于意境的表达。可以看出,丁观加不同于别人的,是他写生和创作时充满了激情,所以,他画中的山水里含有浓烈的感情,画出了意境。
丁观加近年来进步神速,除了他的天赋和勤奋外,还得益于他的读书和思考……他近年来创作的画的精神内涵越来越丰富了。更重要的是,在他现今的创作上显示出旺盛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呈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大家风度。五十来岁对中国水墨画家来说,还不算很大的年龄,我相信,只要他一如既往的坚持传统、写生和创造,坚持学习和探索,他的前程是无可限量的。(1989年)薛永年(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丁观加的山水画进入了语言更趋纯化,意蕴更趋博大深沉,精神感召力更加增强的新时期。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丁观加的山水画已经脱离了纪游山水的局限,向着深入人心的境界飞跃。不但气局更加宏敞,情调更为激越深沉,而且画法也更加讲求笔墨律动与平面构成的浑融无隙。如果仍把他的作品比喻为诗歌,那么以前是随感随发地吟哦平凡动人的眼前风光,这时已经是对祖国神奇山河与悠悠历史文化的深情礼赞。(1993年)李松(著名艺术评论家、原《美术》杂志主编):
丁观加从傅抱石的画风脱出,另寻蹊径。《月色》,月夜是动人的,但“江上生明月”怎么画?他把画面提纯到只是一片汪洋,一抹远山,以重重叠叠的短线,画出鳞麟的江波,线条的交错处,是洒落在烟波之上的散碎月光,他表现的是一种意象,是得长期观察并为之动情的大自然之本色的美。丁观加画的江水有多种性格、多种气象。他用花青,淡墨绂擦出波翻浪卷;用山峦丛树浓重的墨色反衬出波平如镜。他去新疆,创作了《火焰山印象》等杰作,他画了对边疆高山的种种印象:皑皑的白雪,赭红的火焰山,暗黑的帕米尔高原,还有只见一株红叶树的《金色山坡》。有的提炼到只剩几道大的襞褶,却不减其宏伟,那正是异境景象留给这位江南画家的深刻印象。
丁观加和许多江南画家有着颇为不同的审美追求。(1992年)袁林(著名艺术评论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丁观加正是一位有作为的积极探索的画家。他的作品鲜明的时代感即现代面貌,是我的第一个突出印象。
有人认为东西方艺术是不可调和的。从郎世宁开始——包括现代一些大家,都在进行调合东西方艺术的探索,而有些只是折中却不能做到水乳交融。林风眠、吴冠中是获得成功的佼佼者,我以为丁观加也是在这条成功的道路上的前进者。(1992年)马鸿增(著名艺术评论家、原江苏省美术馆副馆长):
丁观加是个头脑清醒、思绪深邃的画家,他选择了一条稳扎稳打、逐步变革的道路。纵观丁观加的探索轨迹,大体上经历了由写实到写意,由繁复到简淡,由平稳到奇崛,由浓重到松秀的变革。(1986年)杜哲森(著名艺术史家、原《美术研究》副主编):
江南水乡人文灵秀,风光旖旎,受其熏陶,在艺术风格上也多淹润空灵,蕴藉隽永,丁观加先生的以往国画创作就具有这一美学品格。但这次展出的作品在艺术风范上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笔墨格制,还是意境构成上,都同以往的创作拉开了距离,显得雄强了许多,尤其是一批新疆写生创作,画的更是丰满厚实,气格沉酣,阳刚之气扑人眉目,不见丝毫的甜腻成分。由此使人想到,人们常说的“超越自我”、“别开生面”等,靠的不仅仅是“内养”,同时还要有“外受”,即冲出固有的文化氛围,投身到一个新的、甚至是陌生的境界中,到那里去观察,去感受,去开启胸襟,充实底气,从而寻找到新的艺术契机、探索出新的艺术语言和艺术节奏,能如此,自然会促成自己艺术的嬗变与升华,真正实现自己的自我超越。丁观加先生的新作,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宝贵的启示。(1992年)左庄伟(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美术批评家):
丁观加对中国绘画传统是尊重和有主见的。他在大学时代就曾受到过著名画家、教授的教育和影响:傅抱石艺术的伟大精深和雄伟气势;吕斯百、黄显之、陈之佛的治学严谨,重视艺术的基础功力;秦宣夫的作画洒脱奔放;杨建侯的勤奋刻苦的艺术创作。这些堪称典范的老师们对丁观加是有直接影响的。
丁观加的山水画艺术植根于中国传统艺术基础,渗透着浓厚的中国民族精神气质。他对人与自然的观念是“合二为一”的。他的那个“大海变成了我,我融进了大海”的梦,正是丁观加的艺术精神所在,亦如东坡居士所云“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比,无穷出清新。”丁观加的艺术正是沿着这个道路发展的,所以说“他的画是地道的中国画,因为他具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
现实生活、大自然不仅陶冶、影响着一个艺术家的情感与气质,而且造就了一个艺术家的独特风格。江南和镇江的山水曾造就了董源和米芾父子,那末,当代产生丁观加就不足为奇了。(1988)张蔷(原北京《美术报》主编、美术史论家、批评家、旅加画家):
90年代的作品,观加兄定力十足,才情达到高峰,无论笔墨、线条、设色都得心应手,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其实这些仅属艺术手艺人手中的艺技,当代画人中不乏其才,何足说三道四。他的过人之处则在于画面背后蕴藏的那个,那个什么?那个自性,那颗心,那个才气。《两棵树》、《河滩飘香》两幅画题迥异,一个戈壁牧场,一个江南河滩,表层画面图像巨大的落差给与人视觉差异,然其底蕴是受同一自性的主持和支配着的;《山不在高》和《岁月悠悠》、《山云水》一以贯之,观加兄自性的艺术释放,包涵在与创作媒介的生宣纸渗浸特质、笔毛软硬柔刚的相异、石质水色的不同品性诸多方面以及墨色水藉以毛笔接触纸面时的运动轨迹里面,有形的绘画形象诉诸人们的眼目,任凭众人评说去。
我自认蛮熟识观加兄,我最佩服他恬静淡泊的心态,亲近自然,视日月、烟云、树木、水流、花草、泥土、山石、沙漠……等等等等都是平等众生,他不曾想着役使他们,利用他们,竟是祈求理解和融合他们,追寻精神的合二为一的境界。(2000年)陈见东(江苏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美术批评家):
丁观加先生隐约体会到烟雨蒙蒙与源泉混混之间的内在联系。于是,他开始了近十年的画水艺术变革,并获成功,创立“丁氏水法”。这种独特的技法从他的作品中才能看得更具体些,无论在手法和视觉效果上均有十分独到之处。他通过水、墨、色交融程度的不同,水分、墨色的干湿浓淡的有机区别,还有留白的经营位置,又把印象派的光影手法稍作改进吸收到画面之中,给人波光粼粼颤动着的视觉愉悦享受。他越发地把“水”的清透、虚怀本性表现了出来,朝霞、阳光、月色、夕阳乃至星空的光线,都通过这种手法体现在画面里。(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