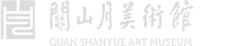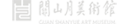- 陈章绩,走过一个时代
-
陈履生
-
陈章绩这一代画家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美术史上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出生在20世纪的30至40年代,童年时代的记忆是战火纷飞,而学习和成长于50至60年代,又充满了理想和激情。在1949年之后,他们遇到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生命的际遇与火红的年代迸发出一个时代的乐章。
当陈章绩1961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时,因为时代的变化所开展的关于中国画的讨论已成定局,新国画的新主张,不仅打破了传统中国画的僵局,也为传统中国画适应新的社会开启了一条新的途径。广东阳江人陈章绩身处广东这个新国画的阵营中,自然会耳濡目染于这个“新”字,而这个“新”字,经他的老师辈关山月、黎雄才、杨之光等的诠释,使他明确了艺术的方向以及时代的使命。显然,这种具有时代特点的表现,发生在陈章绩的身上,首先可以从1954年以笔名陈诺发表于《南方日报》上的《秧田除虫》看出这种时代的印记。这时候他仅是一名中学生,他没有从《芥子园画谱》出发,也没有在梅、兰、竹、菊中寻找走向艺术之途的兴趣,更没有像当代艺术学生从石膏素描中获取基础技法以越过高校的门庭。因此,他的起步就已经表明了这一代人的不同寻常之处。
1957年,陈章绩由阳江一中高中毕业并考入武汉中南美专国画系。这一年最高国务会议决定在北京、上海成立中国画院,这预示着传统的中国画在新中国的新生,也给许多学习中国画的年轻学子展现了未来的希望。在陈章绩的师长辈中,关山月、黎雄才、杨之光于1954年分别创作了《新开发的公路》、《武汉防汛图卷》和《一辈子第一回》,均在当时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的代表性作品。而这一年,关山月在参观鄂北水利工地后又创作了《山村跃进图》。老师的示范性影响,以及以创作带动教学、以体验生活加强艺术基础的教学方法,为陈章绩奠定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而艺术观念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又为他与生活建立起了一个难以割舍的联系。1958年上半年,陈章绩和老师同学到武汉郊区体验生活,创作了国画《归途》(入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国画小辑》);1958年在中南美专南迁广州之后,他又到广东新会等地体验生活,创作了国画《鱼米之乡》(入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农村新景》画集)。1960年,在关山月、黎雄才、杨之光等老师带领下,他和同学赴湛江堵海工地劳动3个月,回校后,师生合作了大幅国画《向海洋宣战》。时任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班长的陈章绩,就是这样在一个下乡与创作的轮回中,度过了大学的生涯,并且通过这一特殊的教学方式,掌握了绘画的技巧与创作的方法。
1961年9月,陈章绩毕业留校,任国画系助教,同时教附中毕业班的国画人物课。1962年,他在东莞、虎门农村的人物速写,基本上能够代表这一个时代中由美术院校培养的人物画家的写生能力和水准:不管是人物头像速写,还是生活中的群像速写,国画人物画中的学院派特点,通过对生活的体验而得到了发挥。这一年,他还兼任国画系一年级的花鸟课。毫无疑问,当时以人物画为教学和创作中心的时代特点,使花鸟画退居到一个非常次要的地位。其中的问题是,花鸟画难以表现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题材,即使有些牵强附会的表现,也是非常有限,远不如人物画和山水画。因此,选派陈章绩教一年级的花鸟画,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只能看作是一种工作的需要。而陈章绩在花鸟画方面的实际水平,今天我们只能通过他1961年在广州文化公园所作的写生海棠,以及这一年在东莞虎门体验生活所画的《虎门拾翠》册页和螃蟹写生,看出他的写生能力,也可以据此了解到他与花鸟画的一些关联。或许是这种有限的关联演变为后来的必然,1963年8月,陈章绩由广州美术学院被派往中央美术学院进修国画花鸟,师从李苦禅、郭味蕖、田世光诸位先生。
就师承而言,岭南地区的花鸟画独具特点,且影响力几乎涵盖了这一地区。它与同时期鼎立并存的京派、海派表现出了强烈的地域性文化特色,同时,它的创新意义也表现出了时代潮流中的传统国画审美现实化的趋向,以及形式技法中更多地融合西法和日本画画法的特点。但是,它为人们所垢病的则是远离传统。而京派在京派文化的笼罩下以传统派据称,虽然被创新派批评为保守,可是,其对传统笔墨的承传,则表现出中国画传统笔墨语言在文化上的持久力量。从文化交流的意义上来说,陈章绩的北上进修,无疑打破了地域文化的局限,使岭南特色中更多地融进一些传统的笔墨,以延续中国画的正脉。因此,他被选派则更多地反映出了一种战略性的安排。
20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画家,因为其突出的写生能力,所以,在人物画创作中都有杰出的表现。而当这一能力施之于中国画的其他领域的时候,不管是转行山水,还是兼攻花鸟,首先在一些基本的表达上都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平,因此,由写生而进入创作几乎成了学院派画家成长的基本规律。李可染、张仃、罗铭以及同时代的画家,正是通过写生获得了改造中国画的成果,当然,南国的关山月、黎雄才也是如此。而关山月、黎雄才这些眼前的老师辈的经验,对于陈章绩来说,可能更直接。所以,陈章绩1962年赴粤北瑶族地区体验生活,不仅画了一批人物及山水画,而且还在阳江举办了“粤北写生画展”。显然,花鸟画的问题不同于山水画,如果纯粹画一些写生可能难以达到花鸟画的境界,因为,那个时代人们对于花鸟画的愿景,除了希望能够表现出时代的新意之外,还希望它能够看得出之所以称为花鸟画的一些语言上的特色。也就是说人们还是愿意在花鸟画中能够看到笔墨的味道,以弥补被改造的中国画所失去的笔墨的不足。
花鸟画的造型与笔墨,所表现出来的一些规律性的问题,正是陈章绩在强化笔墨的进修中所要解决的。在60年初就已经开始的逐渐政治化的氛围中,这种对于笔墨的迷恋显然不合时宜,但是,教学的目的正好像毛泽东所认可的画人体模特儿一样,却以闹中取静的方式,获得了一时的安逸。从另一方面来看,陈章绩却于此失去了人物画创作中的作为。可是,他在这一时期所找到的笔墨感觉,以及运用笔墨能力的提高,却为他后来的创作奠立了基础。其意义在于,一是脱离了写生的状态,二是在岭南风格的基础上增添了文人的意味。这二者作用于他后来的花鸟画作品中,可以说是受益终身。
遗憾的是,他的这种努力没有能够得到深化。因为,在花鸟画的范围中,笔墨的修炼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也需要在技术上的不断磨砺。可是,“四清”运动开始后,这一代人都参与其中,使得他们各自都为之耽误。1964年上半年,还在北京进修的陈章绩赴北京怀柔县杨宋各庄参加“四清”;9月,回广州美术学院后,又带国画系三年级学生到中山县参加“四清”。此后,直到“文革”开始,他们这一辈人都在运动中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好时光,而因此停止了艺术前进的步伐,甚至走了一段难以叙述的弯路。1969年,陈章绩被抽调到广州军区卫生部画中草药标本画,这完全是因他所有的花鸟画的经历,在这不幸之幸中,他有了画画的机会。后来,他被调往广东省美术创作组,这又是一个特别的历程。因为创作组给了年轻画家们一个历史机遇,他们不仅有了因创作展现才华的机会,更重要的这是一个难得的画画机会。对于许多不能画画的画家来说,这是令人艳羡的。陈章绩从这一时期开始,又回到了创作、回到了人物画的队伍中,宣传画《唤起工农千百万》(广东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国画《曙光初照》(入选广东省美展),都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应该说,“文革”时期的广东创作群体是这一时期中国美术舞台上一支特别的力量,不仅是群星闪耀,而且每有新作出来,都一鸣惊人。
1971年9月,陈章绩被调回到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教素描、花鸟以及构图课。在教学之余,他不仅没有放弃创作,反而因创作出现了转机。1973年,他创作的《春闹葵乡》入选全国美展,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并由多家出版社出版。此后受外交部委托,为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和驻各国使馆重画了9张,后来又相继入选英国伦敦的“国际博览会”和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35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可以说,《春闹葵乡》为陈章绩在绘画创作上赢得了社会声名,同时也为他在创作上树立了自信。因此,他1976年创作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1975年创作了《战鼓催春》,1977年创作了《云海哨兵》,并被对外文委选为出国展品,赴日本、美国等国展出。可以说,陈章绩于这一时期进入了一个创作的高峰期,直到后来进入毛主席纪念堂国画创作组及应广东省政府邀请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广东厅作画,他的艺术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总结陈章绩在70年代创作的特点,基本上都是将人物和山水结合起来,表现出特定的时代主题,如:《曙光初照》(1972年),《春闹葵乡》(1973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1976年),《井冈山朱砂冲》(1977年),《云海哨兵》(1977年),《巡逻图》(1978年)。他的这一特点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之内的山水画家的共同特点,只不过像陈章绩这样的人物画家,在画面中把人物缩小到一个有限的面积之内,使人们在类别上更多地是将其画认定为山水画,那么,这对于绘画的多方面素养的要求,已经超越了人物画的范围。然而这对于素养全面、能画的陈章绩来说,正好发挥了自己的特长。而这一专长的发挥,又为他后来专事于山水画创作做了前奏性的铺垫。
从70年代后期开始,陈章绩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国画教学上,培养了很多学生,其中有许多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画创作的中坚力量。而人物画出身的陈章绩,也于这一时期彻底放弃了人物画,只是偶尔在山水画中看到一些点景人物,反映出与人物画的关系。
以花鸟画著称的陈章绩,选择花鸟是因为教学需要而不完全是因为兴趣或喜好。他步入花鸟之途,却在一个始料未及的路途中感受到了发展花鸟画的重重困难,尤其是写意花鸟画,这是一个有着相当难度的类别,因为前人已经造就的高峰,为后人的逾越增加了很多的难度。好在陈章绩具有很好的写生基础,以及转益多师的师承。他吸收了李苦禅的鸟、郭味蕖的花卉、关山月的梅花的诸多优长,在传统花鸟画的结体中,传达出自己的一种笔墨感觉,当然,他也引进了一些具有南方地域特点的花卉,使他的花鸟画透露出一丝南国的新意。他像许多花鸟画家那样,仍然没有离开梅、兰、竹、菊这一文化的概念,所不同的是,他将其穿插于花卉之间,使自然的色彩与文化的墨色形成对照。陈章绩的花鸟画,结构谨严,笔墨沉稳,绝无浮躁之气,像他的人一样。或许是受到关山月先生的影响,陈章绩也专长于梅花,不过他更加强化笔墨于此中的趣味,更加强调一点文人的感觉,不管是红色没骨的梅花,还是水墨勾线的梅花,虽然强调老干,但不求繁华。
陈章绩的山水在脱离了写生之后,将往日生活中对自然景观的印象与山水观念结合起来,以山高水长的方式表现与人们相通的山水观念,同时,传达出笔墨在山水中的作用。他非常精心地处理崇山峻岭与烟云出没,并不时地透露出这一代人为人的规矩、为艺的诚实。他在笔墨中表现的自我,不事张扬,是当代很难得的令人尊敬的品格。正因为他的山水具有这样的特点,所以,需要耐心地品味。1997年6月,为迎接香港回归,香港《大公报》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邀请陈章绩等三位教授为其创作三幅大画。陈章绩的画被选挂在接待大厅,画面磅礴的气势受到人们的称赞,至今,凡来访《大公报》的国内各省、市代表团及海外相关团体都会在其画前摄影留念,故有着广泛的影响。
如何像齐白石那样以衰年变法带来新的变化和跃进,无疑,也是人们对陈章绩的一种期待。从时间上论,生命中的这一时期已经历经沧桑,人和事,包括笔墨,都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一个无我之境在一个大象无形的艺术世界中的发挥,可能会给未来的陈章绩的绘画带来新的面貌,当然,这也是这一代画家在新时代的共同机遇。
一个时代的画家有很多相似的经验和发展的历程,陈章绩与他那个时代的画家在学院教育、政治运动、主体创作、拨乱反正、自我反省、重新完善、继续前行的阶段性过程中,表现出了时代的反映。他们像一部美术史中的一个章节,有历史的无奈,却又难以回避。他们作为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环节,有着作用和影响,特别是对于20世纪中国画发展来说,更以其复杂性和多样性呈现出一种值得玩味的历史意义。
(陈履生 国家博物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