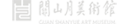- 拙朴风骨
-
中国美协理事、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美术》执行主编 / 尚 辉
-
大写意不单纯是笔墨的简率恣肆,更是艺术家生命情态与个性独立的揭示。徐谓墨葡萄的狂怪野乱,寄予的是他一世的狷介孤傲;八大山人翻白眼的水鸟,隐喻的是他被诛灭族姓、苟延挣扎的敌视与无奈;而傅抱石的飞瀑豪雨,展露的是只有“往往醉后”才能从现实挣脱、纵笔释放的豪情与洒脱。大写意中国画,是留给那些生性就特立独行、命途多舛并与现实社会发生激烈冲突与碰撞的艺术家去燃烧生命的艺术。对于这一类艺术家而言,写意如同打开他们郁积已久的地壳,喷涌而出的是他们生命的火焰和岩浆。
尚连璧的中国画就属于这种类型。他个性豪爽直率,爱憎分明,犹如他早年的黑白木刻,执刀向木没有丝毫的犹豫。他侠肝义胆,宽厚好客,如若他气满乾坤的写意用笔,再空疏的留白都会注满侠义豪情。他不会见风使舵,更不善用虚伪的言词藏掖着自己真诚的良知,政治上的幼稚、为人间的不设防,让他在意识形态浓厚、需要伪善规避风险的时代受尽辛酸的煎熬。但常处逆境,反而锐化了他刚烈的性格,恰似不断淬火的钢铁,刚硬却也易脆断。那些时刻能喷出火焰的愤闷长久地积压在他的内心,大写意像他独自酌酒一样,已成为他宣泄情感不可须臾离舍的通道。在笔者看来,那常常不是创作,而是倾诉,是他一个人在现实找不到出口的一种宣泄与哭号。气足意长,不拘小节,意之大写者源于他生命的幻灭。
他像他的恩师傅抱石一样嗜酒。笔者相信,在“文革”他被批倒斗臭的岁月,是那些劣质浊酒支撑着他的生命。也是从“文革”后期,他逐渐从版画转向中国画创作,并越来越沉迷于傅抱石飞瀑豪雨的境界,仿佛那种笔墨的洒脱是他精神的一种幻景。他学得抱石师那种恣肆挥洒大气磅礴的气度、那种直捉大自然魂魄的灵性和不拘古法的笔墨情致,但作为一个曾受到写实绘画教育并从事过油画与版画创作的画家,其山水画又不可能完全肖似,师其迹不若师其心,这反倒成就了他独特的艺术面貌。相形之下,他的创作增强了破墨散锋皴的表现张力、完善了色彩意象的独立性和凸显了自然山水的构成意识。
傅抱石能够“往往醉后”、在画面上纵横挥扫直呈他的艺术个性,无不得益于他创造的破墨散锋皴。这种笔墨语言改变了传统皴法一笔一画的书写过程,将众多皴法纳入一管,以激情作燃烧的速度将胸中“意象”于顷刻间吐纳画面。破墨散锋皴以其特有的虚实互融而生动表现了烟雨之中的山光水色。但特征有时也成为局限,特别是对于那些仅习得“抱石皴”皮毛的画家而言,破墨散锋皴常得其烟景的朦胧而失其写意的神采。尚连璧的画作往往大胆地强化散锋“骨力”,提高了这一皴法的表现强度。毫无疑问,这种被添加了“钢筋”的破墨散锋皴,也增强了山石造型的建筑感表达。在《黄山之冬》作品里,那种硬挺枯涩、隐现自如的皴线,不仅有助于万木潇落、白雪茫茫之中的黄山俊俏秀拔意境的表达,而且皴线本身就富有张力的美感。在《黄山云烟》里,这种皴法上的“骨力”既展现出浑厚苍茫,也表达出活脱灵动的品质。而《太湖雨意》近景坡岸对于骨力式皴线的运用,不仅无伤豪雨如注的烟景描绘,而且其本身就是情感的物化。
所谓色彩意象的独立性,就是色彩在营造意境上的非从属于墨的独特作用。在包括傅抱石在内的传统山水画里,色彩的运用一直处于被抑制的状态,意境的营造主要依托于“墨分五色”的皴擦处理,即使用色,也必定是“以墨化色”。随着西画传入中土,西洋色彩观念也逐步为中国画家所吸纳。在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接受过完整的学院美术教育的尚连璧,自然而然地把一些色彩观念糅入他的彩墨创作。譬如,《垂帘霜染》的墨色只占很少的比重,而霜染的深红色则充盈满纸,并被提高了色彩的饱和度。垂帘霜染的意境营造,假若没有这样铺天盖地的惹眼的红色,假若没有这样单纯而浓烈的深暖色调,那绝对不会产生这样醉人的秋色。秋天的色彩是丰富浓烈的,而对于冬日雪景,尚连壁也能画出细微的色调。《银装点江寒》几乎没有浓深的墨色,代之则以银紫色充盈天地之间,丛林、浅滩、坡岸被晶莹的厚雪覆盖着,沉浸在纯洁而温馨的暖融融的调性里。银装点江寒虽银装素裹,却毫无冷寂肃杀的氛围,其清旷、朦胧、充盈的情愫,完全取决于画家对于银紫色调的运用。《秋意图》、《霞阳辉映》、《垂帘霜染》、《银装点江寒》和《南山积雪》等这一系列作品,已清晰地呈现了他通过色彩调性营造意境的探索方向。
但意象色彩的独立性,又必须限制在中国画的范畴内,掌握色与水和墨之间的度便显得尤其重要。在《垂帘霜染》和《银装点江寒》等作品里,如果没有水色渗化在宣纸上生成的独特品质,并以此作为大面积的铺垫,那么,其魅力就逊色得多。水色渗化在宣纸上诱引出的独特品格被画家反复用于山水的渲染中,《霞阳辉映》和《南山积雪》就是在这种铺垫的基础上,于近景中点染纯厚浓烈的色彩完成意境营造的。彩墨色调为尚连璧的山水画带来清新、明丽、欢快、蕴藉、饱满的情愫与意境,这既是他早期西画训练和多年油画创作实践打下的色彩功底的自然流露,也是他融入中国画笔墨之后的创造。
或许,走出了“以墨化色”局限的尚连璧,也比他的同龄画家更具有现代性的审美体验与创造诉求。所谓现代构成意识的凸显,正是在这个前提下的不期而至。在《绿荫渔家》、《垂帘霜染》、《沙鸥点点清波远》和《霞阳辉映》等作品里,人们可以看到画家已把自然形态的山水转化为有序的点、线、面集成的山水,从而体现出较为自觉的平面构成意识。无论《垂帘霜染》中红叶低垂像帘子似密排的纵线,还是《沙鸥点点清波远》中用宽笔排列出的几块序列化的横面构成的渚岸,也不论《绿荫渔家》里从天而降富有节奏感的几条纵向“绿荫”,还是《银装点江寒》里晶莹的雪花所构成的充满意蕴的色点,都展示出画家在自然形态的景致里自觉探寻的平面化的韵律与节奏。
尚连璧的山水画虽出自傅氏笔墨,却更多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当代画家对于现代视觉文化的审美体验与审美认知。而这种富有现代文化特征的视觉经验,也无时无刻不渗透到他的花鸟画创作里,从而赋予那些直呈了他的拙朴个性的花鸟画以现代审美气息。
多得益吴昌硕笔墨风骨的尚连璧花鸟画,老辣生拙,浑厚苍茫。像吴昌硕将金石之趣转用于绘画一样,尚连璧早年的木刻创作不仅使他腕力深厚,而且执刀向木的那种快感无形之中都被巧用到花鸟画的用笔方法上。尚连璧的木刻从不以优美流畅取胜,相反,他往往钝刀刻木,追求汉画像石那种稚拙古朴的韵味。当他把这样一种审美经验转用于花鸟画的用笔时,出笔的冲劲、猛劲和狠劲,也自然形成了他果敢、豪放与泼辣的笔性。而且,这种笔性往往被发挥到极致,似乎非猛无以果敢,非冲无以豪放,非狠无以泼辣。他的花鸟画追求视觉上的好看,乃至追求攫取眼球的张力,如敢于铺垫大面积的墨块,强化墨白对比的力度,使形象更富有质感和量感等。用色也更为纯正浓厚,并通过激昂喷涌的泼、洒、滴、点等表现性方式,宣泄响亮、高亢的色彩强度。色彩的浓烈、墨块的凝重,被他猛狠生辣的笔性提升到一种精神意态的表现中,从而也凸显了他意写的大气象、大格局与大境界。
从天风海雨式的散锋皴到钝刀刻石般的浓笔重墨,尚连璧的中国画始终凸显着他不受束缚的旷达个性,也始终透露着他力求破除一些稳定的审美图式的创作企图。不论山水还是花鸟,他出笔的浑朴刚猛和构思的出其不意,常常给人以某种惊叹和震憾。破局和出位,似乎是他的作品始终表现出的一种精神品质。或者说,表现性的浑厚,破坏性的拙朴,宣泄性的豪放,都构成了尚连璧一生艺术创作的人格与风骨。在这种人格与风骨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他的孤独、他的挣扎、他的醉态、他的燃烧、他的坚守和他的创造。
写意之大,在于他立于天地之间厚重浑朴的胸襟与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