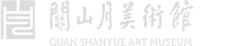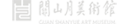- 另一种现代性
-
Michael Kahn-Ackermann (阿克曼)
-
——中国当代水墨画的考察
世界当代重要艺术家中,生计上不仰仗西方艺术的现代性,忤逆其席卷一切的洪流,固执找寻自己当下路径的例子寥寥无几。
水墨画的艺术见解、艺术要求与我们从西方艺术史中熟习的立场迥然不同。这多少能解释,为什么水墨画不像中国当代先锋艺术那般风光,在东亚文化圈之外就没有多少人关注了。
中国的水墨画植根于两千多年的古老传统。“文人画”产生于11世纪,深受禅宗参禅影响,对水墨画产生的根本性的塑造力延续至今。“文人画”的特征在于拒斥对自然的现实主义模仿,彰显内在体验;基于学养、艺术训练和直觉经验的写意性的“自由用笔”;限于笔墨纸为器具;结合书与画;具有稳定分类的图式规范(花鸟画、山水画、人物画等)。在文人画内部还存在众多支流和学派,禅宗和道家对其精神的影响与正统儒家不相上下。
文人画绝不能代表中国古典艺术的全部,对现代水墨画发展产生影响的还有其它形式和流派的绘画,诸如宋代院体写实传统、宗教壁画、民间艺术。鉴于影响的主要方面,本文只涉及文人画的精神遗产和艺术遗产。
还原到内核,“文人画”形式的水墨画可以这样来描述:它是以在宣纸上用笔来直接表达强烈内在体悟的艺术过程,艺术家通常要经过多年的训练才能将这种体悟和表达方式烂熟于胸,以便作画时挥笔而就,看起来即兴和信手拈来。与西方的绘画技艺不同,水墨有其一过性,在落笔之后便不能再修改。
笔与纸的接触既是感性动作,也是精神行为,是一个隐去物质的物质化过程。因而,笔触不仅仅是勾勒,通过界定边缘来赋予形式,它并不“描画”,而是“书写”。这一点能够解释中国美术中绘画和书法之间牢固密切的关系。几百年发展起来的如此众多的用笔技法,必然促成迥异艺术气质和经验的充分发展。品评一个作品时,熟谙丹青的饱学之士更多依据“下笔”的功夫,用笔的神采,而非画作内容和原创性。
当代水墨和古典水墨一样,除了手艺熟巧和渊博的文化修养外,都要求高度的专注、自律、以及对对象和自我的穿透力。人格与生活阅历跟天赋一样不可或缺。水墨画大师佳作常常出现在晚年,
当代水墨和古典水墨所不同的是,不论个人好恶如何,过去的文人都有共同的教育规范和价值准则;不论个人成就如何,都有同属精英阶层的意识。这些为昔日的文人画家提供了自我认同的稳固空间,也提供了艺术家与鉴赏者之间的理解前提。传承下来的图式储备给艺术的自我探索和自我表达提供了广为接受的图像语言。这个空间如今已经不可挽回的丧失了。
同所有当代艺术形式一样,水墨画必须面对21世纪的生活现实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变迁、物质变迁和精神变迁。与中国先锋艺术不同,水墨画无法肆无忌惮地诉诸于西方现代性的资源,艺术家被抛回到既没有传统庇护、也没有意识形态保障的自我体验中,他只能重新创造自己的主题、自己的图像语言。
很显然,当代水墨画的处境维艰。一些受官方追棒和学院派的水墨画家在当今中国国内的艺术市场被炒至天文数字。这非但不是反例,倒是恰恰表现出中国当代文化正处于危机状况之中。回顾150余年来的中国文化史,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危机的来源。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戏剧性的社会和文化巨变,中国水墨画的反应是在支离的现实和过时的传统中寻求逃避。这一时期几乎全部是无力、空洞、人云亦云的绘画。少数艺术大家——如齐白石(1864-1957)——的革新尝试没有产生深远的影响。
悲剧性的是,如同整个中国艺术,水墨画在20世纪上半叶被强制走的道路,后来证明是歧途,政治颐指气使的“现实主义”掩埋了中国自身传统的源头,同时也阻碍了在发现西方现代性的过程中进行丰硕的对话。数十年之久,中国对世界艺术没做出什么贡献。
当中国艺术界在20世纪初试图为中国指出一条通往现代的道路时,他们发现了现实主义,而政治稍晚又将其奉为圭臬,这时,现实主义在它的故乡欧洲已然是明日黄花。只有在纳粹和斯大林的极权统治下,现实主义才被定为信条。
中国艺术早在欧洲之前就明察了它的无力,并将现实主义贬斥为不可取的艺术方法。早在十一世纪,“士人画”(文人画)的奠基人之一苏轼(1037-1101)已经将写实的艺术追求说为“论画与形似,见于儿童邻”。
水墨画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强制婚姻所导致的灾难,既是政治上的,也是艺术上的。不是齐白石,而是法国沙龙传统画法训练出来的一位在艺术上乏善可陈的画家徐悲鸿(1895-1953)成了现代中国水墨画之“父”。现代中国水墨的表达时至今日依旧构成持久性的问题:官方钦定的现实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肆虐,破坏了水墨画的精神根基与艺术根基,使其沦为彻头彻尾的技术手段。它作为“文化遗产”依然在学院被传授,得到无数国家艺术机构的保养,能被确保的无非是现代水墨的行尸走肉。
当中国艺术在上世纪80年代初酝酿着摈弃现实主义信条时,20世纪西方艺术的整套装备都任其调遣。年轻的艺术家带着发现的乐趣和顽皮,运用现代西方的种种技巧与风格,尽管引起国家文化官僚的警惕,却为他们在西方画廊和国际艺术市场开辟了道路。对刚时过境迁的毛时代的“革命浪漫现实主义”的反讽嬉戏,被解读成“体系批判”,获得西方媒体和策展人的垂青。后现代的无拘无束——掠夺所有时代和文化的形式语言与图像世界,给了先锋艺术家利用周边无孔不入的媒体世界和消费世界的影像洪流的自由,他们也同样利用自己的文化遗产,以便给全球艺术界提供所需的地域色彩。
与之相比,当代水墨画则是境遇窘迫:与自己传统的源泉隔绝,无法真正介入受西方塑造的全球艺术势力。当代水墨画要么固守由国家支持的循规蹈矩的学院派,要么尝试在形式上借鉴20世纪的西方艺术,比如表现主义、抽象主义或者其它西方艺术流派,以便在现代性中找到一条道路。两种做法在艺术上都鲜有作为。
1985年,批评家李小山的《当代中国画之我见》一文引发轩然大波,他宣称:中国画从根本上没有能力回应现代的精神现实和审美现实.它不过是历史遗留的过时艺术形式而已。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为了抵抗这个判决,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回答,需要全新的一代艺术家,他们是肇始于八十年代后期的所谓“新文人画派”。这个名字容易引发误导,其实这些艺术家风格迥异,但是存在某些方向上的共性,即他们以不背负任何意识形态的方式应对水墨画传统。他们鲜明地区别于中国先锋派,自我理解成自身文化传统的更新者,他们原则上肯定传统,不否定现代中国的社会现实。
大部分“新文人画”作品偏向形式性、逃往理想化的过去并且强调装饰。不过,他们当中的一些作品成功地把水墨精神与中国瞬息万变的生活世界的经验结合在一起,开发了一条新的道路。
中国八十年代的先锋派主要回应的是中国当下历史的政治经验和社会经验,与此不同的是,新水墨反思的首先是与水墨本质相契的私人的、个体的体验。在古典绘画中少有出现的自我肖像,成为当代水墨画家常常直接反映的内在经验意象。身体、情欲和性在当代水墨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绝非偶然。尽管这些作品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亲熟,它们依然彰显出与古典文人画在审美标准和道德标准上的断裂。古典文人画颂扬出世的孤独感,并将其理想化,这种孤独感表达出几乎所有重要当代水墨作品的根本体验,只不过当代水墨作品没有了古典范本的英雄主义的和田园生活的内涵。
抽象给当代水墨画提供了另外一条路,发展出一种当代的自我图像语言。我们可以同样看到它与传统的亲近和隔绝。文人画自古以来的操作便是与抽象临界,却从不曾超越这个界限,通过用笔和墨色变化,古典大师表现出了复杂的灵性与情感体验,具象内容逐渐消融于近乎纯粹“戏笔”,与抽象仅一步之隔。但是越过个界限有它的风险,这就是抽象容易变成肤浅的、纯形式的游戏。
显然,水墨画难以融入21世纪初这个由消费刺激和媒体呈现所主导的世界,正如同它难以消受20世纪极权的大众意识形态的美学教条一样。水墨的力量在于一个充分体悟、充分展开的自我表达,这种表达要求的绝不仅是发明一个可重新辨识的方式,抑或一个当今艺术市场需要的品牌。
在中国艺术界,当代水墨画一直被排挤在边缘,完全被中国先锋艺术的成功所屏蔽。直至几年前情况才有所好转。近几年来,水墨画再次日益获得关注,得以展出、收藏,也得到批评家、以及完全用其他路径和技术创作的艺术家的重视和讨论。
很多在过去以西方典范为中心采用不同于自身文化和艺术传统的媒介的艺术家,目前开始强调自身文化身份,“中国性”变成年轻一代艺术家的关键词。在时尚潮流之外,中国当代最成就斐然的艺术家中,不乏几位几乎同时开始,同新水墨画家一道,以自己的方式探讨水墨画的艺术遗产。
现代水墨画的更新与发展,既要求对自身文化遗产在精神上和技法上高浓度汲取,也要求试探着与之分道扬镳。它不得不回应当今全球艺术的美学标准,并申明自己的个性。与中国当代先锋艺术不同,水墨画没有对中国后社会主义消费社会进行反讽的、戏谑的、玩世的或悲观的再现,而是采取了一个与之对立的立场。
对于我们这些不熟悉这门艺术的西方观众,这次展览应有助于唤起好奇与理解,去了解一个迄今尚未被关注的“另一种现代性” 。
南京,2012年5月
翻译:王哥